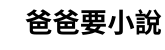由於沒什麼事情。
一個上午的時間,我都在休息室裏面打遊戲,同時在思考着以後的路該怎麼走,雖說東昇裝潢公司已經開起來了。
但目前來說,還遠遠不夠。
人永遠想一步登天。
我也是如此。
所以我在打遊戲的同時,也試圖讓自己戒驕戒躁,然後一步一個腳印的去走,至於和曹天一的過節也可以慢慢去等機會。
不過我也不禁莞爾的在想,不知道當年越王勾踐隱忍十年是怎麼忍下來的,我是一天都忍下去,不僅僅是因爲曹天一羞辱我。
更因爲他當着我喜歡的人面前羞辱我。
誰願意在喜歡的面前露出軟弱不堪的一面?如果不是如此,我也不會在李輕眉面前會如此的患得患失。
下午一點,辦公室的門被推開了。
李麗麗神色焦急的進來了,剛看到我便急着說道:“林東,你快下去看看,有人過來鬧事。”
“有人鬧事?”
我愣了下,蘭桂坊是李輕眉的店,而李輕眉身後站着顧衛公,哪怕蘭桂坊沒有保安,誰又會喫了熊心豹子膽過來鬧事?
不過我也沒多想,在李麗麗說完,我便立刻跟着下去了。
一樓大堂。
一男一女正站在前臺的位置,男的在三十出頭,有着一張漂亮到精緻的面容,往那裏一站,身上便透着一股高人一等的意味,冷眼打量着蘭桂坊的工作人員。
女的二十出頭,濃妝豔抹,身材很好,也很漂亮,穿着性感,挎着個名牌包包,正站在男人的旁邊,嘴角含着幸災樂禍的笑容,眼神同樣刻薄。
會所大堂領班正在耐心的跟男人解釋:“先生,不是我不讓您上樓,而是會所的規定是這樣的,爲了保護客人的隱私,所以不可以讓男人上樓,您要是想等的話,可以在一樓等你女朋友。”
“什麼規定不規定的?”
男人居高臨下,冷笑的看着面前的領班:“老子花錢了,想上去怎麼了,你要是決定不了的話,就把你老闆叫下來,讓她親自來跟我說。”
領班叫王清雪。
王清雪想了下:“要不我把您剛剛充值的錢退給您可以嗎?”
李輕眉以前也知道會所的規矩過於嚴苛,不過她對下面的員工曾經開會說過一句話,客人在篩選會所,會所同樣也在篩選客人。
如果說有客人對會所的規定不滿意的話,可以隨時退錢銷卡。
不過李輕眉這樣做,非但沒有讓會所的生意一落千丈,反而讓蘭桂坊的名字徹底在濱海上層富婆圈打響了,主打的就是高端,隱祕。
所以王清雪跟男人解釋了一會,見解釋不通了,便決定給他退錢銷卡。
不過她沒想到的是她說退錢的話卻刺激到了男人,男人原本還能冷笑的,聞言,臉上瞬間浮現了一抹戾氣,一巴掌就抽在了王清雪的臉上:“我他媽在意那十萬塊錢?”
他身邊的年輕女伴也雙手環胸露出了一抹嘲弄的笑容,很是有優越感的看着王清雪。
王清雪被一巴掌打的臉火辣辣的疼,眼淚含在眼眶裏面,憤怒而委屈的盯着眼前面色有些猙獰的男人。
與此同時,大堂的諮客見男人打王清雪,也憤怒的質問:“你憑什麼打人啊,清雪姐都說了退你錢了!”
男人對身邊的聲音全然不顧,原本他對上會所的樓上就沒什麼興趣,他過來的目的只有一個,那就是見李輕眉。
到了現在,男人已經沒了耐性。
到現在,他索性也不再裝了,望着王清雪,淡漠的說道:“十萬塊錢對我來說,不過是零花錢,沒了就沒了,但你說要退我,這就有點打我臉了,所以給你一巴掌讓你長長記性,現在給你個機會,把我帶到你們老闆辦公室,今天這事我就算了,原諒你。”
王清雪聞言不可置信的看向了男人。
怎麼也沒想到他打人不說,還說要原諒她,到底是誰錯了?
不過王清雪能夠當上大堂領班,也是有素質的,忍着委屈,拒絕說:“我們李總是不會見你的,你要是退卡的話,我可以給你辦退卡。”
“這麼說你是不給我面子了?”
男人聞言突然衝着王清雪笑了起來,只不過笑容裏沒有一點笑意,透着毒蛇般的陰冷,彷彿隨時有再次動手的趨勢。
這個時候,我和李麗麗剛好從電梯裏面出來了。
然後便看到了站在王清雪面前的男人。
在看清楚他的一瞬間,一股憤怒瞬間便立刻從我內心深處湧了上來,曹天一,當初就是他在一次面沒見過的情況下,突然拿着反曲弓指着我,然後說要射我三箭。
也是他讓我這段時間輾轉反側,總是睡不着,被內心的仇恨和羞辱給驚醒。
不過我暫時忍了下來,然後腳步不停的來到了王清雪的身邊,故意當做沒看見曹天一的轉頭問王清雪怎麼回事。
而王清雪看到我也是找到了主心骨,對她來說,我是會所唯一的男人,而且我名義上雖然只是李輕眉的司機,但是我每天和李輕眉成雙入對的出入會所,她們都知道。
所以她們也會在私底下八卦我和李輕眉之間是不是在談戀愛。
見我問起事情經過,王清雪便立刻把剛纔的事情說了一遍,並且旁邊的漂亮諮客也看着曹天一對我氣憤的說道:“東哥,他剛纔還打清雪姐了。”
我剛纔過來的時候,就已經看到了王清雪半張臉上的紅腫。
不過我卻沒有問,也沒有提。
我之所以不問,也不提,是因爲我知道曹天一的身份,常務副市長的兒子,說不定幾年後他就會變成市政府一把手的兒子。
這種人物,打一個工作人員一巴掌叫事情嗎?誰又能找他麻煩?難道真的說報警,說他打人?普通的派出所又敢抓他嗎?
現實永遠是形勢比人強的社會,有時候就是壓着你不得不低頭,讓你忍氣吞聲,讓你憋的發瘋。
但是人真的要永遠低頭嗎?
低頭低久了,會不會從脊椎骨的位置就開始彎了,然後再也抬不起頭來了?
是的,我不甘心,從射箭館回來的時候,我的內心便一直在扭曲,燃燒,我在恨自己,恨自己當初爲什麼要那麼軟弱。
我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報復回去,甚至想到了陳燕朵這條線。
如今曹天一給了我第二次直面他的機會,我竭盡全力的忍着心裏的衝動,抬起頭,目不斜視的看着曹天一,然後語氣緩慢而平靜的說道:“充的錢現在退你,你可以走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