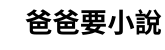現在我命令你們,對於這一切嚴謹透露一個字,與此同時,你們也將會被限制在軍方的科研基地,有先天強者駐守的科研基地!”
中科院空了,僅僅六個小時的時間,中科院便成了一個空蕩蕩的鬼屋,空的嚇人。
所有人資料、器械、人員,全部轉移到了可以抵擋核彈轟炸地下科研基地,有他們開始研究進化液和生物戰甲,雖然趙學五可以提供無比詳盡的材料,甚至每一個步驟都寫得無比詳盡的材料,但是那裏面有很多東西卻不是地球上的東西,所以他們也只能不斷尋找替代品。
不過這一切,現在趙學五已經顧不上了。
在離開了中科院之後,趙學五他們又來到了古老的別墅。
“再說正事之前,我先給你們將兩個故事。”本來趙學五想要說豫州鼎的事情,但是突然想起了他突破先天那天遇到的老八路,還有今天迎接他的那些老人。
趙學五沒等着古老和一號開口,便陷入了回憶當中,“這個故事發生在我的一個朋友和他朋友身上,我朋友有個朋友愛喫水爆肚,經常拽着我朋友在哈市的大街小巷尋找hui民餐館挨家試喫。後來被他找着一家,就在經緯街上,門面不大,衛生條件也讓人不敢恭維,不過爆肚確實做得很地道。一段時間裏,他們經常去那饕餮一番。
那是去年秋天的一個下午,他們兩個又坐在那個小館裏推杯換盞,不是午飯時間,店裏只有他們兩個老回頭客,飯店小老闆也拎杯啤酒坐他們兩個旁邊閒扯,這是個很慵懶的午後。在他們要第二盤水爆肚的時候,一個老乞丐推門而入。
飯店地處繁華地帶,經常有落魄者和僞裝的落魄者來尋求幫助,他們也都見怪不怪,這家小飯館的小老闆挺有人情味,每逢有這樣的事,或多或少他都要給兩個,今天也不例外,沒等老人開口,他掏出一塊錢遞了過去。老人不要,聲音很含混的說不要不要,不要錢,有剩飯給一口就成。
這令他們很詫異――這是一個真正的‘要飯’的,他不要錢。我朋友不由得仔細打量老人,他得有80多了,身板還算硬朗,腰挺的很直,最難得的是一身衣服雖然破舊,但是基本上算乾淨的,這在乞丐當中絕對是很少見的。
要說要飯要到飯館裏是找對了地方,可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。小飯館做的是回頭客生意,客人喫剩的東西直接當面倒掉,他們家主食是燒賣,現要現包。小老闆根本就沒有剩飯剩菜給老人,很明顯他也不能給老人來上這麼一份現要現包,小不其然的一件事就這麼不好解決。
他們的桌上有一屜燒賣,每次來他們都會要上這麼一份,我朋友一口沒喫過,我朋友那哥們也是淺嘗輒止,之所以要它是一個習慣。這家飯館的服務員很有一套,在你點完菜後,她會隨口問一句:‘來幾屜燒賣?’口氣不容置疑,你會下意識的選擇數量而不能拒絕他們家這個祖傳手藝。
他朋友也對這個老人發生了興趣,招呼服務員把這屜小老闆引以爲榮的燒賣給老人拿過去,並且讓老人坐在他們旁邊的桌上喫。沒有外人,小老闆也就不攔着老人坐下,還說桌上有醋,有芥末,想用隨便。
老人喃喃的道謝,從隨身的包袱裏掏出一個搪瓷茶缸想要點水喝,這個缸子讓他們喫了一驚,班駁的缸體上一行紅字還可以辨認――獻給最可愛的人!我朋友這個哥們是不折不扣的將門之後,他祖父是55年授銜時的少將。看到這個缸子出現在這麼個老年乞丐手裏讓他們很納悶,他朋友遲疑地問老人這缸子哪來的?
老人喃喃的說:‘是我朋友的,是我朋友的,是發給我朋友的。’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,他朋友說:爺們,你過來坐,你過來坐,咱爺三嘮嘮。老人說不用不用。
我朋友起身把老人扶到他們桌前,於是就有了這樣一段對話――
‘老爺子,你參過軍?’
‘是呀是呀,當了七年兵哩!’
‘您老是哪裏人?’
‘安徽金寨的。’
‘哪年入伍呀?’
‘46年,就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。’
‘您參加的是哪隻部隊啊?’
‘新四軍六師,就是後來的華野六縱。’
‘您還記得你們縱隊司令是誰嗎?’
‘王必成啊,打仗是好手啊!’
老人語言含糊不清的唸叨起來,我朋友和他朋友都默然了――一個來自鄉下的老農顯然不會知道這些已經逐漸被人們淡忘的歷史,這是支我朋友軍歷史上的英雄部隊――孟良崮上,張靈甫被這支部隊擊斃,使該縱隊一戰成名。
他們給老人夾菜,倒酒,繼續他們的話題――
‘後來還參加了抗美援朝?’
‘是呀是呀,美國人的飛機厲害呀,我朋友就是在朝鮮受傷後才復員的啊!’
‘那您參軍七年應該是幹部了,怎麼是復員呢?’
‘沒有文化啊,當不了幹部。’看見他們狐疑的神色,老人着起急來:‘你們兩個娃不信嗎?我朋友有本本的,有本本的!’
老人慌慌地在懷裏摸出一個包得很仔細的小布包打開來,兩個紅色塑料皮的小本,一個是復員軍人證書,另一個是二等殘廢軍人證書。老人慢慢捲起左邊的褲管,我朋友看見了一條木腿。
他朋友在包裏又拿起一張疊的很仔細的白紙打開看,看完後遞給我朋友,默默無語。
那是一張村委會的介紹信,大意是持該介紹信者爲我朋友村復員殘疾軍人,無兒無女,喪失勞動能力,由於本村財政困難,無力撫養,特准許出外就食,望各地go-vern-ment協助云云。村委會的大印紅的刺眼。
他們都被這個事實震驚了,飯店老闆也目瞪口呆,好久他才結結巴巴的對老人說:‘老爺子,再到了喫飯的時候您就上我朋友這來,只要我朋友這飯館開一天,您就……’
老人打斷他說不,他說他還能走動他就要走,老人說:‘東北人好咧,當年在丹東他就知道東北人好咧。’
我朋友納悶地問老人爲什麼在行乞的過程裏爲什麼不要錢呢?
老人突然盯着我朋友說:‘我朋友當過七年兵的,我朋友還是個黨員哩,我朋友怎麼能……?’
那一刻,我朋友淚流滿面……”
趙學五說的眼珠子發紅,古老和一號也是深深嘆了一口氣,其他巨大巨頭一時間神色也有些複雜。
“還有另外一個故事,發生在我身上,還是突破先天境界之前那一天,在那之前,說真的,來京都這麼多次,我還不知道真正的天安門是不是跟照片電視上一樣漂亮雄偉莊嚴,還有小時候看了那麼多清劇,也沒去過故宮,從小打到唱國歌唱了這麼多年,用我們的血肉築起新的長城,可是長城到底是什麼樣子的,我不知道。
於是那天我的第一站就是天安門!看看升旗儀式。
當我們趕到天安門廣場的時候,廣場上已經有了很多來看升旗儀式的人。
我們緩步走在廣場上,看着那旗杆,看着期刊前方紅色的天安門,一時間感到一股莫名的神聖和莊嚴從心底升起。
隨着時刻的到來。
6名護衛隊員從天安門中心拱形城門整齊走出,英姿颯爽,步伐矯健。護衛隊踏上金水橋,軍樂團奏出了豪邁響亮的《歌唱祖國》的樂曲。方隊穿過長安街,來到國旗座杆臺下。36名隊員分東西兩側站立,護旗手和升旗手登上升旗臺。只聽護衛隊長一聲令下,軍樂團齊奏國歌,鮮豔奪目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。
在這一刻,無論男女,無論老幼,都感到了一股莫明的悸動,甚至一個身穿土綠色軍裝的老人,在一堆年輕夫婦的攙扶下,望着冉冉升起的國旗,哼唱着裹着國歌。
雖然他的聲音已經老到模糊不清,雖然他的佝僂的脊背再也挺不直,但是就是這樣被一個老人,卻成了我眼中最挺拔的哪一個。
不知不覺之間,我們的眼睛溼潤了,周圍的遊人的眼睛也溼潤了。
威嚴的軍樂儀仗隊和護旗衛兵、激盪的國歌和翻飛的國旗,匯聚成蒼宇下的神聖。
在那些直立仰望的男女老少相貌各異的臉龐上,雖然滴落着淚水,卻也袒露着同一種莊嚴與豪情。
這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情懷,不到天安門,不看國旗儀式,都難以體會這種情懷,如果真的要形容的話,能把就是很多人來之前,只是想看看傳說中升旗儀式,但是當儀仗隊出現的哪一刻,當國歌奏響的那一刻,只要身在天安門廣場,都包含着一股朝聖的心態。
不錯就是朝聖。
這些人當中,有不少人守候了幾個小時,甚至是整整一夜之後,絕大多數人只能看到國旗即將升至杆頂的短暫瞬間,因爲人太多了,朝聖的人太多了,大部分時間,虔誠的人們是在無數個不斷仰起的頭顱間尋找紅色的蹤跡。但是,即使這樣,他們仍然感到滿足,因爲他們到過天安門,看過升旗,體會過在國歌響起時油然而生的愛國之情。
不錯就是這麼一種感覺,國歌到了尾聲,國旗即將到頂點,所有人都仰望着那鮮紅的國旗。
直到國歌結束。
不知道爲什麼,我再一次尋找哪一個佝僂的身影,雖然只是破舊的綠軍裝,雖然攙扶老人的夫婦也穿着破舊的衣服,但是我的心底卻湧起了一股難言的情懷。
這是一個老八路!
一個曾經用自己的鮮血爲我們換來現在生活的老八路。
我看着他們身上的衣服心裏有些發堵,如鯁在喉!”
說到這裏的時候,趙學五的隱隱有些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,甚至聲音都有些發顫,古老和一號他們也是無比沉重的聽着。
“雖然有些老八路,因爲各種原因,國家照顧不到,但是我看得出來,這個佝僂的身影充滿着倔強,這一一個不想給國家造成任何麻煩的老八路。
我記得,曾經學過一篇課文,誰是最可愛的人!
在那一刻卻想說,是他!
儀仗隊要離開了,老八路有些不捨的轉過身去。
在那一瞬間,我突然發現,我什麼也做不了,唯一能做的就是想老兵敬禮,爲老兵送行,不錯,我那麼做了,當時的儀仗隊也那麼做,可是那個儀仗隊卻得到了一個集體處分,我想問問這是爲什麼?”
面對趙學五的質問,古老和一號無言以對,“學五……”
“我還沒有說完,”趙學五沒有給古老他們說話的機會,接着說道:“那個時候,我心裏有一種感覺,我還會見到這個老人,而且會在八達嶺長城,因爲我也是一個軍人,雖然我只是一個參軍沒有幾天,還經常不務正業的軍人,但是我可以體會到那種情懷,天安門是第一站,那麼他的下一站就是長城。
不錯就是那個樣子,在八達嶺我再一次看到了那破舊的綠軍裝,佝僂的身影,每走一步,都要休息很久,但是卻倔強的不讓身邊的年輕夫婦攙扶的身影。
我忍不住向着那老人走去,其實我也說不清道不明,爲什麼屢屢被這個身影觸動內心深處最脆弱的那根弦。
源自同爲軍人的經歷,還是源自身體裏面共同的倔強的血液,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當我走過去的時候,那對年輕夫婦也露出普通人樸實的笑臉。
‘小夥子,當初在哪個部隊服役的。’老八路,雖然年紀大了,眼神也不好,但是還是很快注意到了我的到來,這就是一個經歷過無數殺上廝殺,磨練出來的本能,時間長河無法消磨的本能。
‘9521特別編隊。’
‘現在的老編隊越來越少了!’老八路說這句話的時候,無法壓抑內心的傷感和緬懷。
‘不會,他們的精神長在,雖然番號取消了,但是他們卻如同種子一般,在各種地方開枝散葉。’
老八路笑這說我說的不錯,緊接着老八路便問我,“小夥子,告訴我,你爲什麼離開部隊。”
顯然,雖然老八路跟我不相識,但是對我離開部隊這件事耿耿於懷。
年輕夫婦祈求的看着我,希望我不要生老人的氣,畢竟他們看得出來,我的身份不簡單。
我給了年輕夫婦一個安心的眼神,‘我只是離開了最初的部隊,心裏有些懷念!’
‘哦?這麼說,你還是一個軍人!’老八路露出了一張笑臉。
‘算是吧!’
‘什麼叫算是,是就是,不是就不是。’老八路張口就呵斥。
‘我所在的單位,有些特殊,只能算是半軍事編制。’我當時絲毫沒有動氣的意思。
‘這樣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,不是好事!只有真這個的軍事編制,纔算是一個真正的軍人。’
後來老八路邀請我一起爬長城,他告訴我,當年他們幾句曾經在這裏跟扶桑貴子血戰,也曾經跟****血戰,當年他的傷就是在這裏留下,他所在的連隊,一百二十七人,只活下來三個,另外兩個還是終身殘疾,他所在的營隊,五百七十人,只活下來十八個,營長陣亡了,政委陣亡了……
老八路說這些的時候,淚水止不住的往下流,他告訴我,足足六十多年了,他無時無刻不想着在回到這裏,來這裏看看他擋住戰鬥的地方,來這裏祭奠一下他當年的戰友,想來到這裏告訴他的戰友,心中成立了,首都就在距離他們不遠的地方,只要他們抬起頭就看得到……
老八路還告訴我,現在他看到了,看到了天安門,登上了長城,看到了他們曾經戰鬥的地方,死也無憾了……”
說到這裏趙學五的淚水已經模糊了雙眼,緊緊盯着古老、一號,以及一種巨頭大聲咆哮道:“爲什麼,爲什麼,爲什麼他們爲這個國家奉獻了自己的熱血,奉獻了自己的青春,甚至自己生命,卻連看看天安門,都成了一聲的奢望,直到最後生命之燈將熄的時候,纔可以完成一生的執念,爲什麼?”
趙學五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,縱然他面前是這個國家的巨頭,掌控者,他也沒有絲毫壓制自己情緒的意思,“到底爲什麼?告訴我!難道是鳥盡弓藏、兔死狗烹嗎!”